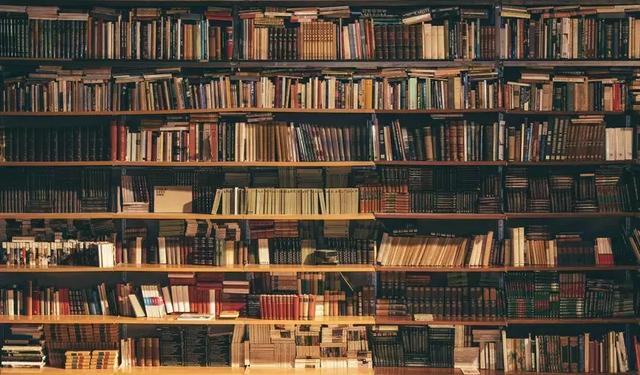|
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說,文學能夠讓人意識到自己缺失的東西,“能夠讓我們明白,像一個人一樣活著并非易事”。 王朔說文學有保護人性的作用,“我不想變成畜生,很大程度上要靠優(yōu)美小說保護我的人性”。 莫言說,“文學讓人心中有愛”。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葉圣陶說,“文學能揭穿黑暗,迎接光明,使人們拋棄卑鄙和淺薄,趨向高尚和精深”。 但是,如果要我坦率地講,文學對我們的用處,只有兩點: 首先,文學是一種純粹的享受。 文學為生活打開了一個逃離的出口,你可以跳進一個故事里,不費力氣和代價地開始一場歷險: 你能從一個地方跳到另一個地方:告別了馬爾克斯筆下的狠熱拉美,馬上就能飛往到劉慈欣書里的黑暗宇宙。 文學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滋味兒了。 生活還是那個生活,你卻有可能成為不一樣的你。 談及愛,你會想到,“老虎融化成黃油,春天里的小熊抱著一起打滾”;會想到“銀河嘩啦一下傾倒在心頭”。 談及美,我們想到的是,“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文學沒有用,但它讓你回歸到生活本身的意義——享受。
其次,文學是我們經(jīng)常視而不見的可靠導師。 當我們遇到困惑的時候,總是習慣在網(wǎng)絡求助。但你很快會發(fā)現(xiàn),能在網(wǎng)上尋找到答案的問題,永遠都是瑣碎的,具體的,短時的,但當你面臨人生中那些無法逃遁的大困惑、大悲傷時,這些回答并不能幫你解決問題,甚至讓你越來越糟。 而文學,卻能用一種靜默的力量給你回答。 比如說,當你感慨自己時運不濟、萬事不順的時候,不妨看看阿城的《棋王》,“棋癡”王一生用他對象棋的執(zhí)迷不悟,告訴你哪些是人生中可以改變的部分; 當你被童年的陰影束縛住時,蕭紅的《呼蘭河傳》會讓你找到久違的陪伴; 當你為情所困時,可以看看張愛玲的《色,戒》,她以痛快淋漓的筆墨,告訴女孩如何與渣男了斷; 至于《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顯然在以他對書籍的狂熱,示范了一個普通人如何在有限的現(xiàn)實中找到自我更新的力量。 文學作品里,有你沒走過的路,沒經(jīng)歷過的事,沒悟透的道理。在人生的某一瞬間,它們會成為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路。 文學是對人生的回答。
但我們?yōu)槭裁纯偸歉惺懿坏轿膶W的用處呢? 因為還沒有形成好的鑒賞力。 文學如酒如茶,并非糖水天生適口。 對好酒好茶的品鑒需要時日,對文學的趣味,自然更需要培養(yǎng)和學習。
小時候看魯迅,老師要求你解釋的是“該段落運用了什么樣的修辭手法,表達了魯迅怎樣的感情”。 閱讀魯迅被當作是一個語文任務,他的文章是需要你拆解的考題。 但大師解讀的魯迅是不一樣的。 拿復旦中文系郜元寶老師解讀的《社戲》為例: 他說,魯迅寫社戲的重點,并不在于臺上的戲有多好看,而在于臺下。 “不是大人們張羅的那臺戲,給孩子們帶來怎樣的快樂。恰恰相反,是孩子們自己在臺下演出的童年喜劇,賦予臺上那出戲以某種意義和美感。” 因此,真正成全這出“社戲”的人,是魯迅的母親。 當孩子們急著要去看社戲的時候,母親寧可自己擔驚受怕,也沒有強行跟孩子們一起去;當孩子們看完社戲回來后,發(fā)現(xiàn)母親已經(jīng)等了他們一整晚了。正是因為母親的尊重,才有了這一場溫暖而美好的社戲。 這就是《社戲》所要表達的思想核心,正如魯迅在《今天我們?nèi)绾巫龈赣H》這篇文章里所說的,大人們應該是“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這樣的解讀,不僅顛覆了我們的認知,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鑒賞文學的方法論。
在《呼蘭河傳》里,看到蕭紅如何在命運的粗糲中找尋童年的溫暖;《圍城》里在女人身邊周旋的方鴻漸,他人生中真正的圍城并不是婚姻;劉慈欣的《三體》,則把我們帶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時空尺度,考驗人性與道德…… |
- 關(guān)注天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