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消息(記者:張博源), 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立項項目《經濟增長與結構演進: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經驗》(英文版)(ISBN:9781631816161)(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偉著,北京大學教授謝世清翻譯)已由國外權威出版機構美國學術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出版社網址: www.AcademicPress.us? ?投稿信箱:manu@AcademicPress.us 或者 AcademicPress@usa.com)于2019年8月正式出版發行。這是美國學術出版社繼出版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中國方言與文化》(ISBN:9781631818844),《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從道安到傅雷》(ISBN:9781631819148) 以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中國經典古詩詞精選100首英譯》(ISBN:9781631819315) 等作品后的有一部力作。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公開發行,谷歌,亞馬遜等主流媒體均有銷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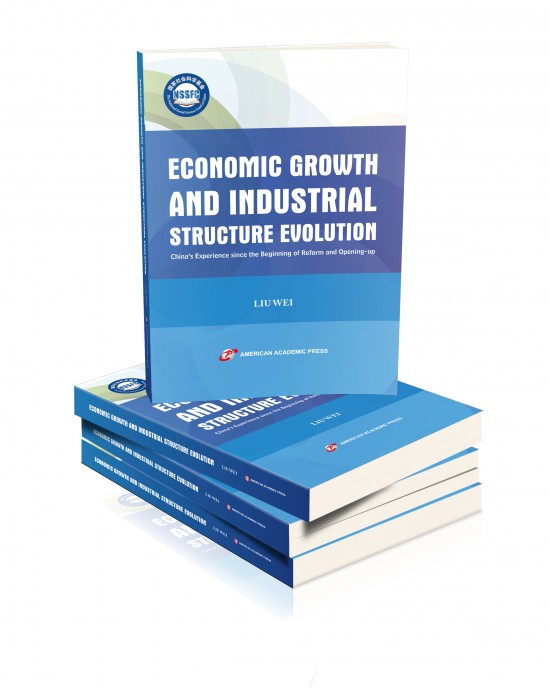 《經濟增長與結構演進: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經驗》(美國學術出版社英文版) 《經濟增長與結構演進--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經驗》共分為七章,分別為(1)“經濟增長水平和發展階段的判斷”,通過應用中國國民經濟核算和世界銀行的各國國民收入統計數據,在縱向上和橫向上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成就和國際地位變化進行了分析和比較;(2)“新常態下的新變化、新失衡、新政策”,討論了在中國經濟增長新的起點上,如何實現可持續的增長;(3)“經濟增長的失衡與宏觀調控”,對如何通過宏觀調控改善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失衡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4)“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化”,對我國改革開放后不同階段產業結構變化的特點進行了研究,指出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化遵循著與世界各國共同的規律;(5)“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效率”,對中國現階段的產業結構高度進行測度及國際比較,描述產業結構演進對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并分析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中突出的結構性矛盾;(6)“產業結構失衡與初次分配扭曲”,從產業部門的角度,研究了三大產業部門的成本結構即初次分配結構對于我國整個國民收入分配所產生的影響;(7)“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結構優化與供給側改革”,討論了供給側改革及供給管理與宏觀調控及經濟結構演變的相互關系,剖析了供給管理和供給側改革所需的體制條件。 作者劉偉劉偉,先后獲得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教,1992年晉升為教授,1994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理論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5年)。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經濟科學》主編,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美國學術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是美國一所獨立的學術性出版社,出版社出版反映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具有學術價值的專著、專題論文、修改后的碩博士論文、原創性資料、教材以及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還出版多種學術性的專業期刊。美國學術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致力于出版國際學術界頂級作品和研究。除了主要出版用英語撰寫的著作之外,還出版用中文、西班牙語、法語、西班牙語等語言撰寫的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美國學術出版社在美國猶他州、佛羅里達州、馬薩諸塞州、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以及加拿大等地均有出版社工作點。美國學術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已經成為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平臺。根據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和中國網的消息,國外權威出版機構美國學術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連續6年被國家社科基金列入國外出版機構指導目錄。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和美國學術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2014年到目前共合作27項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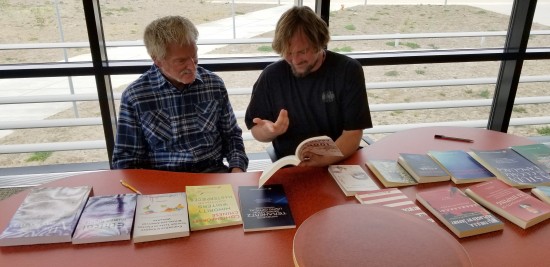 美國學術出版社中文編輯在探討中文書稿 以下是《經濟增長與結構演進: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經驗》(英文版)一書的部分內容: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GDP(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逼近10%,國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大大提高,即便是日本的“神武景氣”和韓國的“漢江奇跡”都未有如此驕人的成績。而拆分來看,這段歷史大體有三個發展階段,1978-1998年,這段時間的中國主要處于短缺經濟狀態,其表現在于需求旺盛,通貨膨脹,為了抑制經濟過熱,政府主要采取了“收緊”的宏觀經濟策略,在1998年之后,中國也由低收入中國轉變成為下中等收入國家。而1998-2008年這段時間,中國經濟表現為需求疲軟,存在通貨膨脹壓力壓力,但整體經濟依然向好,政府采取的政策主要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種松緊搭配。但由于2008年開始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為刺激經濟,國家采取全年擴張的“雙松”政策,既“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比如著名的“四萬億刺激”。這一系列的手段使得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期間仍然“一枝獨秀”地高速發展,2010中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邁入上中等收入國家之列,2015年中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而全球平均人均GDP為10000美元左右,歐美發到國家平均水平約4萬美元,作為處在上中等收入國家之列(共有54個國家)的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差距。 在世界經濟歷史,有不少國家都止步于“中等收入”之列,有的國家經濟開始停滯不前,有的則是經歷了長期衰退,這一現象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拉丁美洲(拉美漩渦)和東南亞諸國(東亞危機)等地區,盡管從表象來看各不相同,但主要根本原因都在于隨著國家進入中等收入之列,社會總成本不斷提高,但產業結構并未作出相應調整,制度落后,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應付國際資本入侵,以至于危機到來時束手無策。這些也都是步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需要警惕和重視的。 201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面臨了新的變化,主要是經濟下行風險和通貨膨脹壓力的“雙重風險并存”的局面(西方在七十年代出現的“滯脹”)。也就是在前兩個階段分別出現的問題此刻都出現了,無論是“松”還是“緊”的政策都可能單獨結局問題,如果采用擴張的政策,盡管可能會防止經濟下行,但有可能造成通貨膨脹,若是采取收縮政策,也許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問題能夠抑制,但經濟下行風險則會增加。因此必須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樣松緊搭配模式,而這種方法與1998年之后不同在于所面對的問題更加嚴峻,也許簡單依靠兩種政策協調難以維系,因為兩種政策方向相反,很有可能作用相互抵消,就好比一個身子虛弱又上火的人,要給他喝綠豆湯降火,又要給他中藥滋補,則綠豆湯有可能化解中藥的藥性。 更重要的是,以調節需求側為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改善”內因“,就如同”打鼴鼠“一樣只是緩解矛盾,而并非解決問題。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一國經濟狀況在需求側看來取決于“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 從消費看,表面現象是需求不足,但消費不足其實在于收入分配出現了問題,有錢的不愿意花錢消費,沒錢的對未來沒有自信而選擇了儲蓄降低了消費傾向,而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在于解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宏觀層面來看,初次收入分配存在問題,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中分配,但企業和居民收入增加速度遠少于稅收增加速度(平均每年增幅18.8%),也就是說減稅工作勢在必行。從中觀層面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存在差距,城市居民收入平均三倍于鄉村居民,而其背后邏輯在于產業間差距較大,農業在GDP貢獻中占據9%,但從事第一產業人員占到30%,按要素分配角度來看,30%的農業人員分配9%的產業收入,自然相對收入要少于其他產業從事人員。從微觀來看,由于歷史、環境等客觀原因,城市居民之間、農村居民之間收入也存在差異。 從投資看,投資疲軟的大體問題在于有融資的渠道缺乏好的項目,即便如大型國有企業,融資快、融資易,但難以有好的項目為投資標的,簡單重復低附加值的投資并不能創造有市場的產品,而是僅僅創造過剩的產品,其背后根本的原因在于結構性問題,企業當務之急應該技術創新,產品升級,對于落后產能應當淘汰,將資源投入到真正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行業中。 從上可以看出,當下一些問題并非是需求管理所能解決的,根本原因仍然要從供給側入手,譬如土地、人力、資源、技術等一系列生產要素,現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資源成本不斷增加,國外也不像過去有許多更為先進的技術讓國內來模仿,這些都對企業的轉型和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供給側改革,就是對這些環節“開刀”,以達到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目標,然而這些問題并非短期能完成,與類似“猛藥”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同,供給側則是漫長的調節過程,這一過程中所包含的特點在于中國的經濟增速由高速降低為中高速(經濟增速的換擋期),前期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需要時間消化(前期危機處理的消化期),以及經濟結構調整需要付出的代價(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三期疊加”的態勢并非短期,所以稱為“新常態”。 西方供給學派主張有“四減四促”,也就是減稅、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促進私有化、促進競爭市場發展、促進企業家精神發揮和促進技術創新。中國目前的背景與供給學派幾十年前所面對的情況早已不同,當下中國處在的環境更為復雜,在借鑒供給學派觀點時,更多應是考慮制度改革,比如減少管制和壟斷,減少稅收和行政審批,著力于結構變化,加強要素的升級,比如技術進步、人才教育、信息化布局等,尊重市場規律,淘汰落后產能及僵尸企業等。 需澄清的一個誤區在于供給側改革并非否定需求管理的作用,二者作用范圍、時間、效果都有所不同。供給側改革也并非否認政府的作用,而是需要政府通過制度紅利改善市場的有效性,但需注意的是,政府通過干預企業自己內部的創新、升級過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計劃經濟”,這與供給側改革的初衷違背,而如果拿捏其中的尺度也是政府和企業在協調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在西方歷史上,面對出現的“滯脹”問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總統都嘗試過“供給改革”,其中也暴露出了些許問題,比如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問題導致產品價格上漲但服務質量下降,稅收降低導致公共支出減少影響了居民的福利,國有企業裁員導致消費下降失業率上升,部分小微企業慘遭淘汰等…而當下的中國是個更為龐大的經濟體,又面臨著復雜的國際局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情況對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為巨大的考驗。 |
- 關注天氣:
搜索



